参加革命是什么体验?
1968年7月,正值文革时期。
某天下午一点,中国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正在负责收听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之声”中文广播,这个广播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对外公开电台广播,可接下来的内容,令他们终生难忘。
“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对外公开机构,“革命之声”则是马共拥有的广播电台名称。
当时“革命之声”中,女声的马来亚共产党人民军战报正在缓缓播送,突然,电台中传来自动武器的射击大作,并且,这枪声在逐渐增多、增大,其中不时掺入几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不久,枪声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手枪的近距离射击声。紧接着,又听到一大群人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在叫喊,随之而来的是女播音员的喘息声,每个人都清楚的听见她了发出的呼喊:各位听众、同学、亲人、朋友们……亲爱的祖国,永别了!
在广播中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后,广播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声响
当时所有收听到这一广播的人,都猜到了这意味着什么。
很多年后,人们知道了这个与电台共存亡的女播音员令人惊异的情况:她姓焦,原是中国山东济南市的一个红卫兵,济南某中学的高三学生,一个美丽的姑娘。
六十年代后期,以支援世界革命为己任的格瓦拉主义,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青年人的欣然认同与接受。因此,一批中国红卫兵自行跨过边界,自发投入到东南亚的丛林中,参加了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来自济南的焦同学,便是其中一员,她成为了马来亚共产党人民军战士,在设于丛林中的马共广播电台,做了一名播音员。
据那份资料说,当时,因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军特种部队的偷袭,在抵抗无效即将被俘的最后时刻,女播音员拉响了一捆集束高爆反坦克手榴弹。
女播音员牺牲1年多后,1969年11月15日。
寂静了许久的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革命之声”的广播,突然,以更大更纯的声音,重新回荡在空中。只是,这个声音,却不再是发射于马来亚与泰国边境的丛林之中,而是来自一个出人意外的地方:中国湖南省益阳县境内的四方山、代号为“691”的建筑群。
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白:安全、稳定、播音质量高。
电台分别以马、泰、华、英语进行播音,每种语言每天播音一到四小时。
此后,长达12年,马来西“革命之声”的广播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不论马共人民军与政府军的交战如何激烈,革命形势如何艰巨,马来西“革命之声”的广播,都能屹立不倒,久久地回荡在空中。
直到1980年6月,这个声音才撤出中国,重新回到马来西亚与泰国交界边境的丛林。
由此,“691”便成为了一段历史,也成为了一处遗迹。
从湖南省会长沙市,向西约60公里,便到了益阳县境,在距319国道只有几公里之处,有一个叫岳家桥的小镇,四方山就在小镇的附近。而隐蔽的“691”建筑群大院,便处于四方山中的一个水库旁,占地面积近200亩。
当年马来亚共产党的“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就设在这里。

更多回答
“革命者投身武装革命斗争时是什么心态”,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
题主预设“革命者参加革命”是“唱着国际歌,拿起枪上战场”,这是一种后人浪漫主义想象,确实很浪漫、很热血,但未免又有些刻板与空洞了——参加革命、武装暴动的人事权一定要懂“因特纳雄耐尔”吗?其实不然。
就拿开国上将洪学智来说,洪学智参加革命前,对马克思主义和赤色革命仅仅是“有所耳闻”的状态,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甚至存在一种传统的排外偏见。(当然,也是朴素的爱国思想)
1926年,洪学智十三岁在双河庙上小学时,双河庙高小的校长余海若、老师刘伯力都是共产党人,为了隐瞒身份在家乡开小学。二人见小洪学智很好学、愿读书,便向他“播撒种子”:在课余时间偷偷给洪学智看《共产党宣言》。
可是,洪学智小小年纪就有朴素的反帝爱国思想,他听说马克思是个“犹太人”,立马反感的不得了——读犹太人写的书,这不是让我去信基督洋教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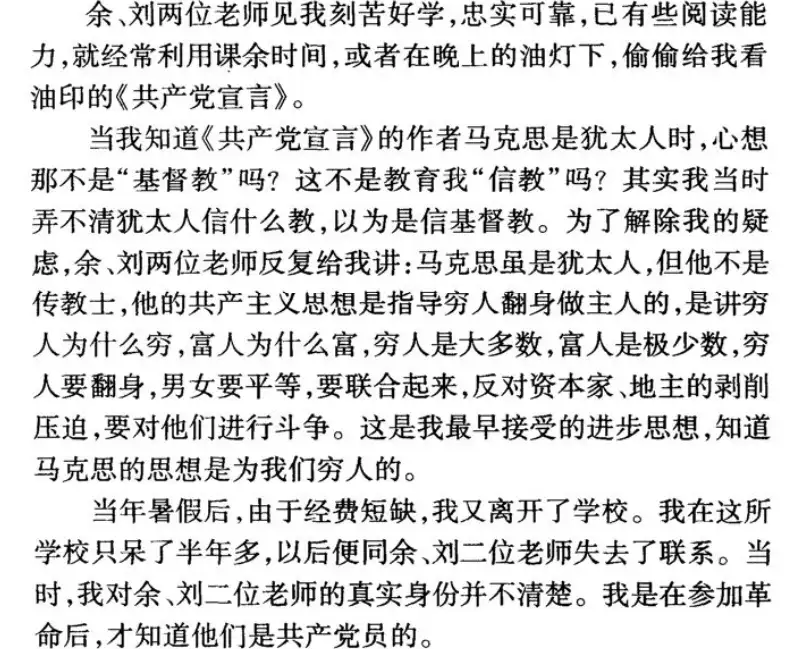
然而洪学智刚刚“开蒙”,没来得及入《共产党宣言》的门,只读了半年书便因家庭的贫困而失学了。1927年的黄麻起义,同14岁的商城少儿洪学智也无什么联系。那时他正在给一个远房亲戚做工,为人家放牛、捡柴,混口饭吃。
当小洪学智捡柴火、赶牲口时,事情正在起变化,商城县民团内部正暗流涌动。谁都想不到,商城民团的一个小班长周维炯(其实在CP那边是商南团委书记),竟然会在1929年趁着饥荒率领手下民团反水,发起农民大暴动……
1928年冬到1929年初的某一天夜晚,十五六岁的洪学智如往常一样干完农活,躺在主家的草棚中休憩。忽然,一个人来到他面前,开口问他:“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联庄队?”
洪学智心里纳闷,联庄队、红枪会之类的组织往往是地主老财主持办的,除了看护乡村,便是给地主撑腰。怎么会来找上自己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他问道:“联庄队不是地主老财的组织吗?”
“不对!我们联庄队跟地主老财的联庄队不一样,公开是防匪防盗,实际是专门吃大户,帮穷人找出路。”黑暗中,那人这样告诉洪学智。
“你们真的是吃大户吗?”
“那还有假,比你在这强多了。”
年轻的洪学智动了心,他与这多年后记不清名字的来人一拍即合,参加了南溪的联庄队,跟着人到了地方一看,发现竟已聚集了上百人——都是跟他一样的穷苦人。大家都是奔着参加队伍一起吃大户来的。

做了几个月吃大户的联庄队后,洪学智一行人接到消息,商城的各路联庄队、兄弟会、穷人会要一起策动一场大起义——这是要做反王了——时间定在立夏那日晚上。届时各路人马一起行动,打豪绅抢地主,之后再往南溪火神庙集合。
1929年的5月6日,立夏节到了,十六岁的洪学智在南溪同联庄队的穷人兄弟们一起暴动,他们挥舞着砍刀梭镖,趁夜接连攻破了几家地主大院,像通俗小说里的绿林好汉一样开仓放粮。一般的农民受了鼓舞,也拿着火炬同他们一起来造反。
此时正同兄弟们“替天行道”的洪学智还不知道,他这回参加的是后来历史上有名的“商南起义……
5月7日早上,参加暴动的各路人马拢共二万人齐聚南溪火神庙蔡氏祠堂,洪学智随大家一起在台下,听着台上领头的几位首领讲话。
“我们这次武装暴动成功了!”这没什么。
“地主任意欺压我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是要建成没有压迫的太平世界。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等,苏维埃是什么?
洪学智听到这,才发觉自己这回参加的,不是过去小说传奇里那样的起义,而是一场赤色革命。且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苏维埃具体是什么,只知道苏维埃是cp的组织,要给穷人做事。
第二天,周维炯等人宣布将联庄队等组织改编为赤卫队、自卫军和游击队,前二者不脱产,游击队则是完全脱产的军事队伍。
此时,洪家老宅早已因为他参加联庄队的事被烧了,家人害怕因洪学智造反的事再受牵连,来信劝他回家。可开弓没有回头箭,洪学智明白这个道理,就算他愿意放弃武装,顾敬之那样的民团首领也不会饶他性命。
于是,十六岁的洪学智成为了赤南县游击队的一员,在一位绰号“老程头”(这绰号颇有农军色彩)的小队长手下做班长。
开国上将的二十余载革命斗争生涯,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开始了——他没听说过红军,不了解什么是苏维埃,还曾一度把马克思当做基督教士。这就是一名老革命、老红军参加革命的开端。

而洪学智这样的革命者不是个例,在出身黄安的陈锡联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事迹。
陈锡联参加革命时只有十四岁,他曾在1926~1927年黄麻地区农运高潮时参加吃大户的活动,他自述当时自己把脸拿锅底灰擦黑,跟着人们一同抢粮,每当自己带着一满袋的粮食回家,那便是“全家最高兴的时候”。
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武汉“七一五”后农运被取消、镇压,农民不准再去吃大户、放仓粮,陈锡联一家又回复到“食不饱,力不足”的窘境中。

我们怎么办?挨着饿的陈锡联开始向往起游击队,在他眼里,红色游击队是一支“神秘”、“伟大”,为穷人救急的队伍——当然,陈锡联也羡慕游击队的绿林生活,他们的日子强过自己这个挨饿的小农民(有时还要做乞丐)
有了“与其全家饿死,不如去当游击队”,“兴许还有条出路”的思想,十四岁的陈锡联再也忍受不了过年时当乞丐讨饭、平日里种一亩地吃不饱饭的生活。他迫切想要改变自己“食不果腹、受人欺辱”的现状。
1929年4月,14岁的小陈锡联,一个再也忍受不了贫苦生活的村童,背着母亲逃出陈陋的家屋,奔入山林,投奔了开国大将徐海东的游击队。


那时的陈锡联,不知道红军,不知道苏维埃,也不太了解党。在参加红军一年,因表现出色被党代表吸收入党时,陈锡联才知道,原来还有“党组织”这种东西!
如果你问1929年的陈锡联,“革命是什么?”他恐怕说不太清楚“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种道理。
他了解的,是神出鬼没、杀豪绅为他报仇的游击队,而他对游击队的了解,也很有限。在小陈锡联的眼里,游击队就是一支从事伟大事业的神秘队伍。“红军”、“苏维埃”都是陌生的词汇,至于“党”,那跟游击队是一个东西!
参加革命时的陈锡联,只是一个对这穷人受欺、富人嚣张的社会不满、愤怒,进而不甘于贫困的“愤怒少年”罢了。

对洪学智、陈锡联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参加革命的体验”,大概更接近于“杀尽不平致太平”。
一群对社会不满至极的年轻穷人聚到一起,在有浪漫思想的“先行者“率领下投身革命,他们不会唱《国际歌》,手里也没有步枪,有的只是原始的竹枪,还有朴素的怒火。
“如果你觉得社会不好,何必去建设它呢,大家都受够了这破民国,不如去推倒重来,另起炉灶。”
岁月不待人,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们现在基本凋零殆尽了,之前看到消息说,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英雄如今只剩17位。高赞回答已经提供了许多关于老战士们的资料,从中我们看出的是水深火热中走投无路的底层百姓的朴素的怒火。但是在这里我想提一下上世纪70年代曾经前往缅甸参加革命的“知青兵”们。他们的心态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两国都在发生剧变。在缅甸,1962年吴奈温政变上台,对缅共的勃固根据地大举进攻。旧勃固根据地远离缅北边境,赛力斯虽有意援助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另一方面,吴奈温政权上台后效仿苏联模式,没收在缅华人财产,导致华缅两族矛盾迅速激化,最后演变成吴奈温当局规模性的排花活动。此事件一出举国哗然。在当时国内也处于特殊时期,上山下乡如火如荼。尤其是云南昆明的知青,基本上都被安排到中缅边境一线的保山专区“外五县一镇”插队。
当时1969-1970年前后越境参军的大体上可以有几种情况。
在一些地方,缅共人民军能直接把招兵处设在中方境内。一些地方军政干部也鼓励边民过境参军。有老兵回忆,一个叫沈子安的战友就是被蛮海边防站的边防战士劝出去参战的,战士们对他说:“小鬼,快出去,在打反动派哩!”遂毅然参军。
还有一些地方,越境可就不能这么光明正大了。一些地方是严禁偷越国境的,擅自越境既有投敌之嫌。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越境参军。一部分人的理由是不愿意参加枯燥的农业劳动。据云南知青高景华回忆,在那一带知青的条件非常艰苦,天气闷热,自己砍竹子搭住处,蚊子多到晚上睡不着,粮食不够,生病了也没有药,每天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进行思想教育。当时与他同一个知青排里的,正是后来的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的主席、彭家声的女婿林明贤。在林明贤鼓动之下,他们一帮人趁着雨夜,携带三天的粮食偷偷跨越国境去缅甸参了军。
还有一些人越境参军的理由要更辛酸。有一些人是在风暴中跟错了队,或者是身份不太好,在当时的环境下留在国内没有出路。
最著名的可能是腾冲女知青潘东旭。她的父母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后来被划为右遭到折磨。她当时16岁的哥哥潘国英气不过,便用石头砸施暴者家的玻璃,甚至趁着晚上去揭过人家房梁上的瓦片,结果被当场逮捕,拿铁丝拴着吊起来。这件事发生之后,潘国英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个月后家里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自己是“光荣的国际主义战士”,并寄来了一张军装照。潘东旭也想用这种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就越境参加了人民军。
笔名“红飞蛾”的王曦也是这样。他的出身还要更恶劣一些,他父亲曾经在军统任职。在站队的时候又站了当时云南的“炮兵团”,结果旋即被打为“反”。他下乡之后,分配到的是更贫穷的陇川山区,与瑞丽坝子的生活状况天壤之别。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越过了国境线前往了缅甸。
他们去缅甸有一个好处。缅共虽然接受援助,但是赛力斯却无权对其内务说三道四,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是吸取了近代第三国际错误的教训,随后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原则。而缅共这边正缺兵力打开局面。所以不管来者出身或者什么不好的记录,只要不闹到引渡的程度,他们就一概接收。
知青大多是从勐古河上蹚水越境的。虽然名为河,其实只是一条十来米宽的小溪。因此中缅边境老百姓将这些卷起裤脚淌过勐古界河的知青志愿兵称为裤脚兵,后来裤脚兵也泛指所有过境参加缅共人民军的所有国人。之后又有一些裤脚兵们见识到战争的残酷后跑了回来,他们被戏称为蘸水兵。还有的人参加人民军就是为了白嫖装备,当兵几天就开溜,除了枪不要,其他的东西全背回国内寄给家人,下一次换个招兵站又过去,有的甚至如此这般挖了十几次墙角,成为了“职业蘸水兵”。


许多知青刚参军,就得知人民军前线遭到惨败的消息。当时德钦丹东也在效仿赛力斯,搞一些大宣传,声称最多三年就能打到仰光。初期确实打的不错,在缅北开拓了局面。勃固方面随即要求人民军南下,以接应北上的缅共核心。结果人民军主力刚南下腊戍就遭到埋伏,一场恶战差点全军覆没,最后是3035的知青营断后掩护。潘国英在战斗中牺牲。为了伏击这名许多知青第一次见到真实的战争,见识到缅军并非宣传中所说的不堪一击。腊戌之战后,和王曦一起参加缅甸革命的15名新兵,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这距离他们趟过勐古河才仅仅半个月。
之后1971年冬天,又爆发了更为惨烈的滚弄战役,人民军孤军深入敌后与缅军正面对抗,损失惨重。随后北方又发生变故,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此事件之后赛国同吴奈温的关系出现了松动。在国内,知青政策也开始变化,回城之风出现,更多知青逃回国内。这就是1972年的裤脚兵回国潮。
1972年以后,缅共宣布不再接收从过境参战人员,之后又开始主动排挤裤脚兵,先是以“企图暴动”为由,试图拆散裤脚兵内的湖南人团体,最后事情扩大波及了不少无辜者;然后又给两名昆明知青顾荣成、齐贵华以出身为由扣上了帽子,就地枪毙;还有1974年的“杜、徐、林集团”案,借其打牌喝酒之际,把中层干部杜士元、李如景和徐文斌三人抓捕,牵连众多,严刑拷打下有人招供说打牌是为掩护暴动,结果事件进一步扩大,多人被就地正法。一系列事件之后,逃兵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有人无法逃回国,退而求其次逃去了泰国。
1980年前后,这边才开始重视裤脚兵的接纳回归政策,但是落实不力。王曦等待了多年仍未办好手续。当时是1985年,王曦不愿意留在败迹已现的队伍,选择当逃兵,用假通行证偷渡回国,回到了昆明。好在1985年5月,王曦终于重新拥有了国籍、户口和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他先是当了7年每天工作可达16小时的机械工人,又下海到昆明某外贸公司任边贸部经理,在人迹罕至的缅北开山伐木,做木材生意,结果随后企业又改制、破产、倒闭。他一生都在社会底层艰难地讨生活。
后来有一些接二连三回去的知青,又在国内遭到冷遇而没法生存下去,选择了重返缅甸。还有一些极少的知青留在缅共,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比如林明贤。在彭家声起事之后,林明贤也宣布独立。
时过境迁,当年的老战士,如今的心绪又是怎么样的呢?《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写道:
在王曦家徒四壁的家里,记者问他,你后悔不后悔,他盯着记者的眼睛说:“我还活着。”
现在,这个老知青,于谋生的余暇,以幸存者的责任感在烟壳纸上、在博客上写起了回忆录。他相信,曾经有过的那种追求,值得骄傲。起码,现在每有老战士死去,昆明都会有个百人以上送葬,他们给死者披上红色旗帜,表示对“革命者”的尊重。
“我想,革命是不朽的。”切·格瓦拉的一句话,或者可以作为这群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老知青的注脚。
